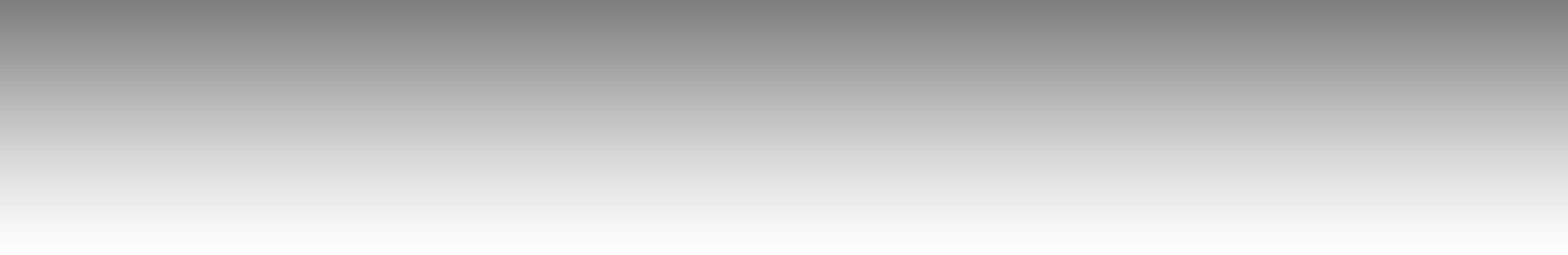今天的復(fù)旦校園里,子彬院與燕園之間隔著一片萋萋芳草。當(dāng)年,這里卻是神秘而旖旎的女生寢室——“東宮”。
“東宮”建于1928年,由一位名叫陳性初的愛國華僑捐資二萬兩白銀建造。這座西式二層磚墻樓屋占地465平方尺,共計43間,可容納148名女生[1]。一間間窗明幾凈,布置高雅大方,門前一圈綠籬,圍著一大片如茵的草地。
由于該寢室地處當(dāng)時校園之東,外觀又為“宮殿之式”,精美氣派,因而被稱為“東宮”。1928年6月,第七期《復(fù)旦旬刊》上最早出現(xiàn)了“東宮”一詞:“宮殿之式建筑甚精,綠窗與紅壁齊輝,足為江灣道上增色。未來中國女文學(xué)家、女科學(xué)家均養(yǎng)成于斯?fàn)N爛宏偉之‘東宮’中,即記者所望也”[2]。有人曾在校刊上這樣描述東宮:“雖無飛檐斗拱,但是它那硬山正脊,分峙兩翼,八道垂脊,鴟吻高聳,也著實壯觀!”[3]
就在興建“東宮”的前一年,一群女生裊裊婷婷步入秋日的校園,正式拉開了復(fù)旦“男女同校”時代的帷幕。
這一步對于復(fù)旦而言,來之不易。1927年的中國,除了幾所只招女生的教會學(xué)校外,鮮有大學(xué)開“女禁”,即使是在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上海也是如此。老校長李登輝擔(dān)心男女同校會牽扯男生心思,敗壞學(xué)風(fēng),曾放出話來:“復(fù)旦要想男女同校,須等我死了以后!”[4]
當(dāng)時正值各地革命運動風(fēng)起云涌之時,校長的四個門徒百般努力加以勸說——“學(xué)校也需遷就時代,目前女子大學(xué)太少,以富有革命精神及領(lǐng)導(dǎo)學(xué)生運動的復(fù)旦大學(xué)不招女生,似乎有違男女平等之原則,一般有志升學(xué)的女子也得不到求學(xué)機會。可否在暑期補習(xí)班兼招女生作為試辦?”[5]終于,畢業(yè)于耶魯大學(xué)的李老校長在深思過后,同意一試。之后,學(xué)校通過層層面試,精心挑選出十余名女生參加暑期補習(xí)班。
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嘗試。一位校友這樣回憶當(dāng)時的情景:“平常一般頑皮而天真的男同學(xué)驟然間見到了這些女同學(xué),好似人力車夫見了交通警察一樣,深恐觸犯規(guī)章、人人謹言慎行、內(nèi)務(wù)整潔。而功課方面也比往昔更加用功,生怕成績落在裙釵之后。”[6]
這樣的場景讓李登輝校長放下心來。1927年9月,第一批女生正式進入復(fù)旦學(xué)習(xí),這些女生有的進入大學(xué)一年級或預(yù)科班學(xué)習(xí),有的則自其他學(xué)校轉(zhuǎn)來,從二年級或三年級念起。女生們所進入的專業(yè),既有像大學(xué)社會科、中國文學(xué)科這樣的文科類專業(yè),也有大學(xué)理工科、生物學(xué)科這樣“被視為高難度”的理科專業(yè)[7]。女生們成績優(yōu)異,在當(dāng)時全市性的外語比賽中包攬第一名和第二名——第二名獲得者因未能奪冠,當(dāng)場哭了鼻子。
“卓爾不群、不讓須眉,大概就是從女生進校那刻留下并延續(xù)至今的傳統(tǒng)。”復(fù)旦大學(xué)校史研究專家許有成說。這份傳統(tǒng),也不斷鞭策著復(fù)旦的男生們,使其倍受激勵,唯恐落于女生之后。
1928年,更多女生進入復(fù)旦,“南宿舍頓時無插足地矣”[8],“東宮”便應(yīng)時而生。
幾十載光陰從搖擺的裙裾間滑過,“東宮”的佳人們留下了眾多逸聞趣事,也留下了自己青春年華里的喜嗔喟嘆。很久以后,當(dāng)她們各自漂泊世間、隨命運的波瀾而起伏時,“東宮”里的那些回憶,或許仍能化為一點星火,溫暖漫長的歲月。八十周年校慶時,幾位年逾八旬的老校友回憶起了“東宮”軼事。
“‘東宮’門口有‘男賓止步’的禁牌,一位調(diào)皮鬼在‘止’字上加了一橫,糾集一群人喊著一、二、一‘正步走’!直奔宮內(nèi),嚇得‘公主’們個個雨打梨花深閉門。”[9]
“只有校慶節(jié)日,‘東宮’才歡迎男生參觀,房間布置得十分雅潔,‘公主’們都逃之夭夭,留下一、二位能言善辯的擔(dān)任發(fā)言人,答復(fù)男士們提出的各種問題。那些表面上裝得一本正經(jīng)的紳士們,卻暗中干著順手牽羊的勾當(dāng)。出宮后,有的袖籠里抖出糖果,有的口袋里摸出腦脂、口紅、香水、手帕,……他們開了慶祝向“東宮”進軍的‘戰(zhàn)利品展覽會’,然后來一個‘失物招領(lǐng)’。”[10]
“有一位女生案頭擺了一個一寸多長賽璐珞做的小棺材被摸走了。她氣得不得了,狠狠地罵道:‘哪個小癟三偷走了我的小棺材,一定不得好死。’旁人聽了,都哈哈大笑。”[11]
“東宮”門禁之嚴離不開里頭三位頗具特色的人物。校友邵夢蘭曾撰文回憶他們:“第一位是門神爺老頭子,我始終不知道,也不曾問過他姓甚名誰,只跟著別人喊他老頭子就是了。這是把門的。他熱心負責(zé),從來不曾放進一個男生過。老頭矮矮胖胖,冬天一身黑直貢呢長袍,夏天穿一身米色紡綢褂褲,穩(wěn)穩(wěn)重重,有三分威嚴,整天到晚坐在門口一張小寫字桌上,里面有兩位,一個叫徐媽,另外一個叫鳳儀,梳一條黑油油的長辮子,一甩一甩地。她是管樓上的。徐媽和鳳儀,都穿短褂褲,鳳儀經(jīng)常喜歡罩一件黑布背心。她是有人會客,先在老頭子那里登記,然后老頭子站在二門邊向里面直著脖子一喊:‘徐媽(或鳳儀),幾號房間X小姐有人會客,那來賓在會客室等’,被請的也就應(yīng)聲而出了。鳳儀是一位姑娘,黑黑的,長一臉的青春痘。做事干凈利落,蠻兇的。我有一次看她跟子彬院的男工友講話,大聲大氣,像一只母老虎。……”[12]
邵夢蘭從復(fù)旦政治系畢業(yè)后便長期從事教育工作,執(zhí)教杏壇逾一甲子,成就斐然。退休后,她還在東吳大學(xué)等校兼課。八十歲以后,她多次出席復(fù)旦大學(xué)世界校友聯(lián)誼會。[13]
第一批進入復(fù)旦的女生中,有一位名叫嚴幼韻的閨秀,長得十分漂亮。在“東宮”建造前,她總是坐自家的轎車從位于靜安寺的家中來校上課。轎車配有司機,車牌號是八十四號。一些男生就將英語Eighty Four念成滬語的“愛的花”。嚴幼韻的父親在南京路上開著“老九章綢布莊”,綢布莊各種衣料隨她挑,因此她每天更換的服裝總是最時髦的,令人眼花繚亂。[14]“愛的花”這一外號于是越來越響亮,以至于后來很多人只知道“愛的花”,反而忘記了她的真名。
嚴幼韻當(dāng)時在整個上海都十分有名。她常常在各種舞會上出現(xiàn),以其風(fēng)姿傾倒眾人。后來,她嫁給了外交官楊光泩。1942年,珍珠港事變爆發(fā),日軍攻占馬尼拉,時任馬尼拉總領(lǐng)事的楊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慘遭殺害。面對命運驟變,嚴幼韻這位幾乎沒有吃過苦的上海灘名媛卻鎮(zhèn)定地承受著一切,含辛茹苦地帶領(lǐng)外交官家屬的大家庭頑強地生活下來——她不僅帶領(lǐng)她們在馬尼拉的院子里養(yǎng)起了雞和豬,還學(xué)會了自己做醬油、肥皂。[15]
與嚴幼韻一同進入復(fù)旦的女生中,還有一位名叫陳瑛的中文系學(xué)生,也許很多人對她的筆名“沉櫻”更為熟悉。陳瑛1927年從上海大學(xué)中文系轉(zhuǎn)入復(fù)旦中文系,1928年在陳望道主編的《大江》月刊上發(fā)表處女作——短篇小說《回家》,受到茅盾稱許,從此步入文壇[16]。
1931年,陳瑛與當(dāng)時任教于北大的梁宗岱結(jié)識,兩人相愛,幾年后結(jié)為伉儷。1944年,身在重慶的陳瑛聽聞?wù)煞蛞魄閯e戀的消息,帶著與梁宗岱所生的三個孩子黯然離去。其后,陳瑛到了臺灣,在斗煥坪,她教書、翻譯,仍一直以“梁太太”自居,署名仍寫“梁陳瑛”。兩人在50年代時恢復(fù)通信聯(lián)系。此后沉櫻籌劃著將梁宗岱的書稿出版,其中甚至包括梁寫給新歡甘少蘇的詞集《蘆笛風(fēng)》。但1982年,重病臥床的梁宗岱希望能見陳瑛最后一面時,猶豫過后的陳卻決定堅守曾經(jīng)許下的“永生不再相見”的諾言,未與梁見面。[17]兩人幾十年的愛恨糾葛成為了一個難以為外人參透的謎。
我國著名的話劇藝術(shù)家、戲劇理論家鳳子也是從“東宮”中走出的女士。鳳子原名封季壬,在大學(xué)時就表現(xiàn)出了很高的表演天分。中文系出身的她文學(xué)功底深,英文功底好,常常擔(dān)負翻譯劇本工作。復(fù)旦劇社的創(chuàng)始人洪深教授覺得她有當(dāng)演員的天才,便引導(dǎo)她參加話劇演出。她成為國內(nèi)第一位演《雷雨》中四鳳一角的演員。鳳子畢業(yè)后到日本留學(xué),在戲劇《日出》中扮演女主角,公演后去拜訪郭沫若。郭沫若和妻子安娜殺雞買魴熱情款待,并在玉版箋上題了一首七絕贈送給她:“海上爭傳火鳳聲,櫻花樹下囀春鶯,歸時為向人邦道,舊日魴魚尾尚赪。”鳳子后來回上海主編純文藝雜志《人世間》,得到了郭沫若、茅盾、沈從文、胡風(fēng)等許多作家的支持。
鳳子的丈夫沙博理是個中國籍美國專家。他定居中國五十年,入了中國籍,當(dāng)選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當(dāng)中,因為江青,鳳子曾有四年時間受到審查。沙博理始終對她不離不棄。[18]
另一位學(xué)者毛彥文女士,曾經(jīng)擔(dān)任“東宮”的女生指導(dǎo),與復(fù)旦女生“相處融洽,亦師亦友,幾年下來,相安無事”。[19]毛彥文青年時代的驚人之舉,是出演了一場轟動江山的逃婚事件。這件事讓她成為“近代中國婚姻史上少數(shù)敢于挺身沖撞傳統(tǒng)婚姻藩籬的一名時代女性”。[20]毛彥文最真誠、最熱烈、最持久、最癡迷的追求者是吳宓。他為毛彥文代取了“海倫”的名字,為“海倫”寫了大量的情詩。直至上世紀60年代,吳宓還請人畫了一張毛彥文的肖像懸于壁上自賞。這份單戀最終無果——毛彥文下嫁給父執(zhí)輩的熊希齡,兩人的忘年戀締造了一段傳奇。
在自傳《往事》中,毛彥文回憶了熊希齡追求自己的經(jīng)過。那時,毛彥文受聘于復(fù)旦大學(xué)、暨南大學(xué),“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,余時在復(fù)旦”。熊希齡內(nèi)侄女朱曦本是毛彥文就讀湖郡女校時的同學(xué)、知己。毛彥文在北京女高師讀書時,常隨朱家姐妹到熊府玩耍。熊希齡一直對其關(guān)懷備至。1934年,熊希齡到滬,住在侄女朱曦家。出于禮貌,毛彥文應(yīng)朱曦之約去看望長輩熊希齡。緊接著,朱曦持續(xù)前往復(fù)旦找毛彥文聊天敘舊,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。毛彥文堅拒。次日,熊希齡親赴復(fù)旦約見毛彥文。同時,熊氏加大攻勢,幾乎每天給毛寫信或填詞寄贈。之后,熊希齡的長女熊芷懷五六個月的身孕,從京抵滬,代父求婚。在這重重包圍下,兩個月后毛彥文終于首肯。1935年2月9日,33歲的毛彥文與66歲的熊希齡舉行了婚禮。
熊希齡生平致力于慈善事業(yè),他去世后,毛彥文繼承乃夫遺志,繼任香山慈幼院院長,長年在桂林、柳州、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業(yè),造福良多。1961年毛彥文赴臺后自動放棄美國綠卡,在臺重執(zhí)教鞭,生活低調(diào)。1999年10月3日,繁華閱盡后的毛彥文溘然去世,享年一百零二歲。[21]
風(fēng)流總被,雨打風(fēng)吹去。當(dāng)年的“東宮”早已毀于日寇的炮火,而“東宮”中那些年輕的身影也逐漸沒入歷史的塵埃。但,見證這一切的復(fù)旦依然存在,帶著那個時代的情懷與記憶,并將繼續(xù)留存下去。
摘自《桃李燦燦 黌宮悠悠:復(fù)旦上醫(yī)老校舍尋蹤》
[1]摘自《復(fù)旦最早的女生宿舍》,載于1986年復(fù)旦大學(xué)校刊,作者:筆樹
[2]摘自《女宿舍新秋落成之預(yù)聞》,作者不詳,載于《復(fù)旦旬刊》第二卷第七期,1928年6月25日
[3]同注1
[4]摘自《復(fù)旦女生,優(yōu)雅作別封建的過去》,載于《新聞晨報》,作者:張計紅
[5]同注4
[6]同注4
[7]資料來源:1927年復(fù)旦大學(xué)在讀女生名單
[8]同注2
[9]摘自《復(fù)旦最早的女生宿舍》,載于1986年復(fù)旦大學(xué)校刊,作者:筆樹
[10]同注9
[11]摘自《從燕園到東宮》,載于1974年《復(fù)旦通訊》,作者:邵夢蘭
[12]同注11
[13]資料來自復(fù)旦大學(xué)百年校慶網(wǎng)站
[14]摘自《復(fù)旦女生,優(yōu)雅作別封建的過去》,載于《新聞晨報》,作者:張計紅
[15]同注14
[16]資料來自百度百科“沉櫻”詞條
[17]資料來自百度百科“沉櫻”詞條及《花落春猶在》(《散文》2012年第8期)
[18]資料來自《鳳子,從楊貴妃故鄉(xiāng)走出來的明星》,載于2007年6月5日廣西日報“花山”副刊
[19]摘自《往事》P29,作者:毛彥文,百花文藝出版社,2007年1月第1版
[20]摘自《民國風(fēng)景》第57節(jié)“毛彥文的往事”,作者:張昌華,東方出版社
[21]此段材料來自《民國風(fēng)景》第57-59節(jié)“毛彥文的往事”,作者:張昌華;以及《往事》,作者:毛彥文,百花文藝出版社,2007年1月第1版